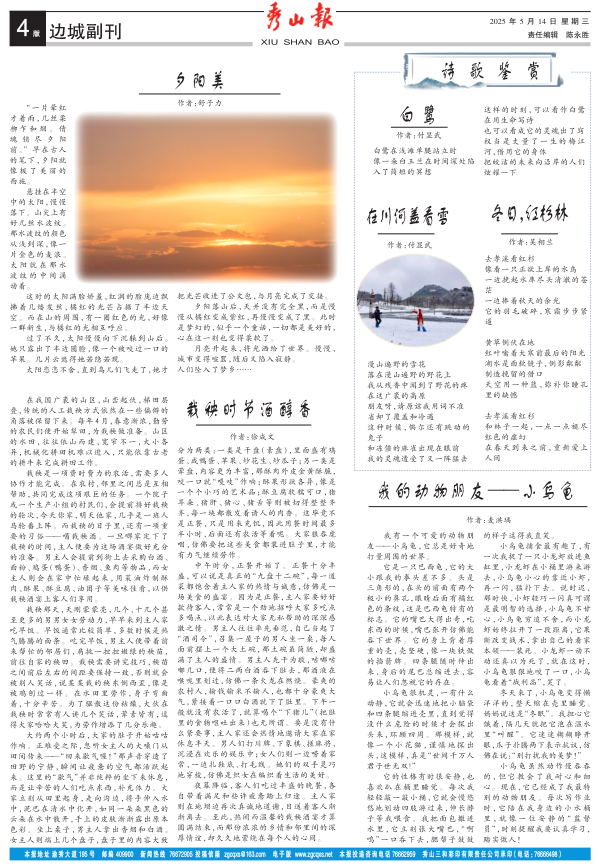在我国广袤的山区,山峦起伏,梯田层叠,传统的人工栽秧方式依然在一些偏僻的角落被保留下来。每年4月,春意渐浓,勤劳的农民们便开始犁田,为栽秧做准备。山区的水田,往往依山而建,宽窄不一,大小各异,机械化耕田机难以进入,只能依靠古老的耕牛来完成耕田工作。
栽秧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农活,需要多人协作才能完成。在农村,邻里之间总是互相帮助,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。一个院子或一个生产小组的村民们,会提前排好栽秧的轮次,今天你家,明天他家,几乎是一班人马轮番上阵。而栽秧的日子里,还有一项重要的习俗——喝栽秧酒。一旦哪家定下了栽秧的时间,主人便要为这场酒宴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男主人会提前到街上去采购白酒、面粉、鸡蛋(鸭蛋)、香烟、鱼肉等物品,而女主人则会在家中忙碌起来,用菜油炸制酥肉、酥果、酥豆腐、油团子等美味佳肴,以供栽秧酒宴上客人们享用。
栽秧那天,天刚蒙蒙亮,几个、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男男女女劳动力,早早来到主人家吃早饭。早饭通常比较简单,多数时候是热气腾腾的面条。吃完早饭,男主人便带着前来帮忙的邻居们,肩挑一担担嫩绿的秧苗,前往自家的秧田。栽秧需要讲究技巧,秧苗之间前后左右的间距要保持一致,否则就会被别人笑话,说某某栽的秧东倒西歪,像是被鸡刨过一样。在水田里劳作,身子弯曲着,十分辛苦。为了驱散这份枯燥,大伙在栽秧时常常有人讲几个笑话,荤素皆有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,为劳作增添了几分乐趣。
大约两个小时后,大家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。正难受之际,忽听女主人的大嗓门从田间传来——“回来歇气喔!”那声音穿透了田野的宁静,瞬间让疲惫的空气都活跃起来。这里的“歇气”并非纯粹的坐下来休息,而是让辛苦的人们吃点东西,补充体力。大家立刻从田里起身,走向沟边,将手伸入水中,泥巴在清水中化开,如同一朵朵黑色的云朵在水中散开,手上的皮肤渐渐露出原本色彩。坐上桌子,男主人拿出香烟和白酒。女主人则端上几个盘子,盘子里的内容大致分为两类:一类是干盘(素盘),里面盛有鸡蛋、咸鸭蛋、苹果、炒花生、炒瓜子;另一类是荤盘,内容更为丰富,那酥肉外皮金黄酥脆,咬一口就“嘎吱”作响;酥果形状各异,像是一个个小巧的艺术品;酥豆腐软糯可口,猪耳朵、猪肝、猪心、猪舌等则被切得整整齐齐,每一块都散发着诱人的肉香。这毕竟不是正餐,只是用来充饥,因此用餐时间最多半小时,后面还有农活等着呢。大家狼吞虎咽,仿佛要把这些美食都装进肚子里,才能有力气继续劳作。
中午时分,正餐开始了。正餐十分丰盛,可以说是真正的“九盘十二碗”,每一道菜都饱含着主人家的热情与诚意,仿佛是一场美食的盛宴。因为是正餐,主人家要好好款待客人,常常是一个劲地招呼大家多吃点多喝点,以此表达对大家无私帮助的深深感激之情。男主人往往率先垂范,自己当起了“酒司令”,召集一屋子的男人坐一桌,每人面前摆上一个大土碗,那土碗虽简陋,却盛满了主人的盛情。男主人先干为敬,咕嘟咕嘟几口,便将二两白酒吞下肚去,那酒液在喉咙里划过,仿佛一条火龙在燃烧。豪爽的农村人,输钱输米不输人,也都十分豪爽大气,紧接着一口口白酒就下了肚里。下午一般就没有农活了,就算喝个“下猪儿”(把肚里的食物呕吐出来)也无所谓。要是没有什么紧要事,主人家还会热情地邀请大家在家休息半天。男人们打川牌、下象棋、搓麻将,沉浸在欢乐的娱乐中;女人们则一边唠着家常,一边扎鞋底、打毛线。她们的双手灵巧地穿梭,仿佛是织女在编织着生活的美好。
夜幕降临,客人们吃过丰盛的晚餐,各自带着满足和些许疲惫踏上归途。主人家则在地坝边再次真诚地道谢,目送着客人渐渐离去。至此,热闹而温馨的栽秧酒宴才算圆满结束,而那份浓浓的乡情和邻里间的深厚情谊,却久久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间。
主办单位:秀山电子报 2020 COPYRIGHT
渝ICP备09056022号 Powered by 秀山网 提供技术支持